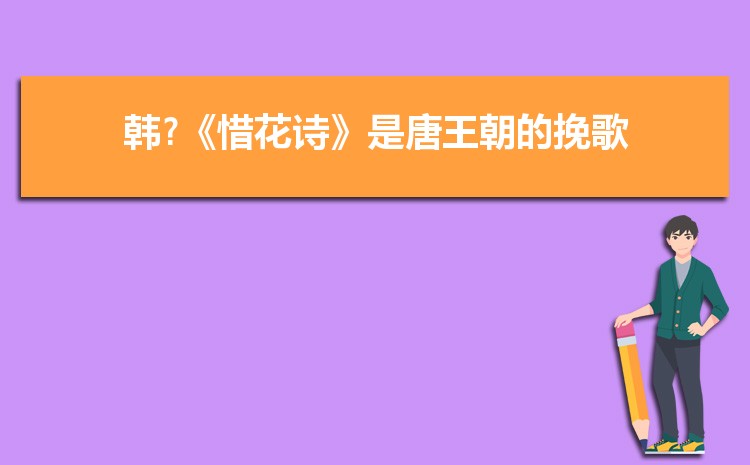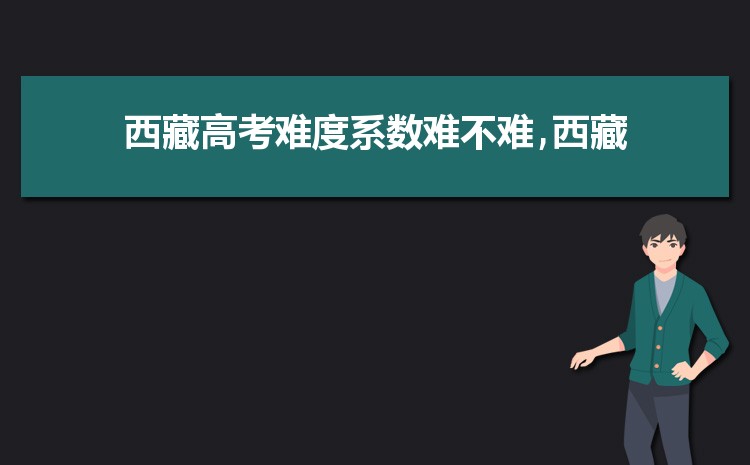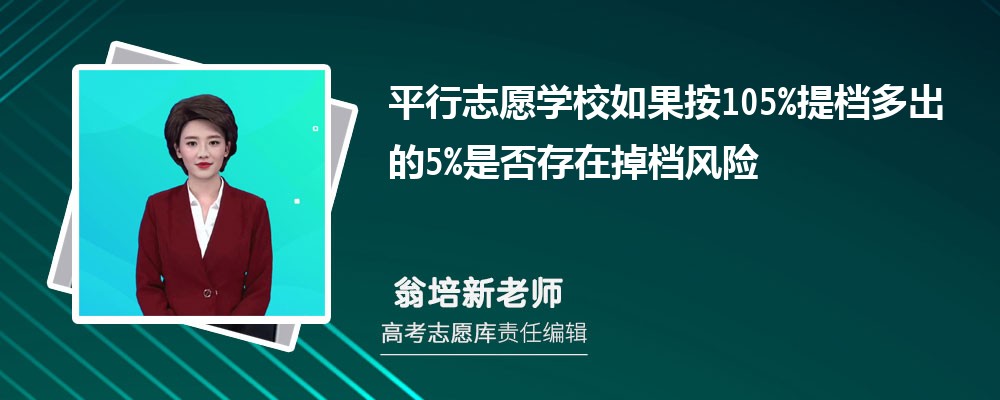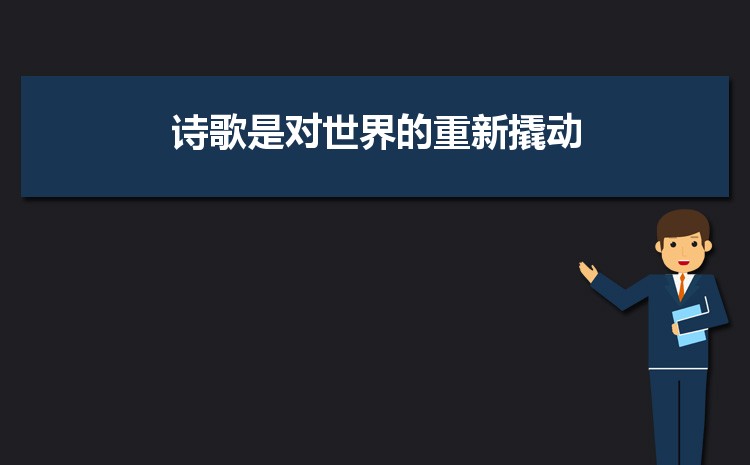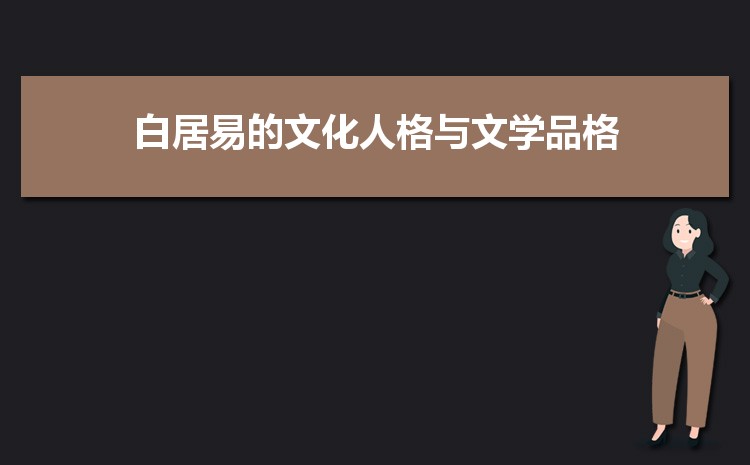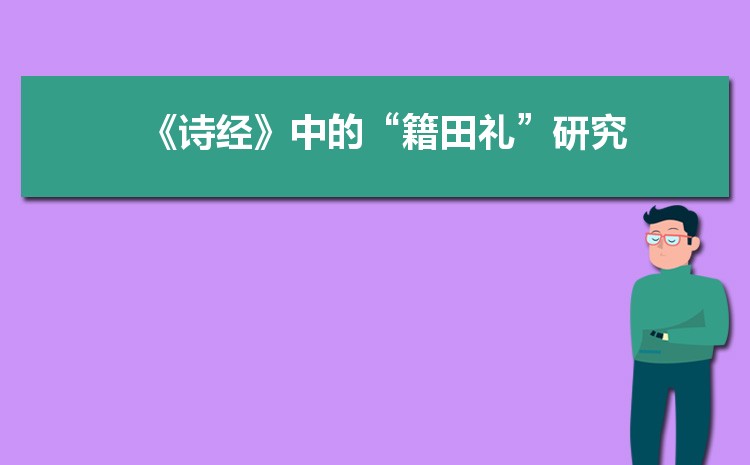猝然遇见语言不通的人们,谁都难免一时尴尬,感到耳口形同虚设。然而,聪明的人类总有办法跨越语言障碍,肢体语言、书写文字,均可用以追求与口语异曲同工。既然比比划划可做“手语”,那么写写画画亦可做“笔语”。汉文化圈的古人们,很早就懂得用“笔语”代“口语”,发明了用汉文笔谈、画谈,还有更高端的诗谈。这“三谈”留下来的,就成了珍贵笔谈写本。
日本明治时期围绕大河内辉声展开的中日文人的笔谈资料,除了部分已有实藤惠秀、郑子瑜(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》,以下简称《遗稿》)、刘雨珍(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,以下简称《汇编》)等的编校本外,尚有部分未经深度整理。这些笔谈写本接下来的研究任务,就是进一步解字、识趣和以意逆志、知人论世了。
笔谈解字
由王宝平主编的全八卷的《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 大河内文书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,以下简称《文书》)使大河内文书在中国出版的梦想,划上了完美句号。这项事业经过了中日几代学者跨国跨代接力,终于由宝平先生等人共同完成了最后一棒。彩印精美清晰,装帧考究得体,精彩呈现了近一百五十年前汉文笔谈的风采,也为笔谈写本研究提供了极佳资料。诚如主编序言所说,大河内文书以其持续时间之长、数量之庞大、内容之丰富、参加人数之众,名列笔谈资料之首。本书虽名曰“笔谈”,其中收录的还有数量可观的唱和、序跋、书信等,是明治时代汉文写本的缩影。
较之那些润饰成篇的文献来说,笔谈最大的特点,还是它的“原生态”,对话有来有往,较少预先备用的官话套话,相对直接真率,对话本身未加他人篡改增删,也可以说更富有一时性和真实性。
异国文人在一起以笔墨代口舌的对话,如果没有碰上对此极为珍惜的对话者,也可能随谈随丢,双方的笔迹飘落在历史的尘埃中,随风吹散,再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。可喜的是以大河内辉声为首的日韩对话者,不仅将其精心保存了下来,而且在当时便做了一定程度的整理。他们在这些随笔中,补充了彼此来往的一些信函,记录了当时对话人员与时间,并且不失时机地添加了相关的信息,这些大大提升了笔谈资料的研究价值。
这些资料影印出来,将其永久保存,就将那一时期那一群不同国籍的人们文化沟通的瞬间定格下来,留给后世的比较文化研究者,没有颠三倒四的评价,原原本本地再现那一刻、那一地、那一群人细微的心灵碰撞。正是有了这些笔谈资料,把没有录音设备的无声对话保留下来,才使我们仿佛亲耳听到那时的来言去语,知道谁问了什么,怎样回答的,谁在交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。这些笔谈,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“笔述历史”。
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,是笔谈得以展开的基础。这种兴趣,包括了对许多文化细节的兴趣。患有“文化冷漠症”的人,不会有这样持久的对话;而满足于概念认同的人,也不会抓住其中看似细枝末节的点滴不放。笔谈将彼此对对方文化的认识具体化,也更加增进了对对方学识人品的理解。笔谈者随时在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,也在表明自身的文化观。日本人的中国文化观,中国人的日本文化观,百年来虽多有变迁,但其中也有一些属于久远的议题。笔谈开始的是一个文化面对面的时代,那时的话题还有许多没有完全过时。
笔谈不拘场所,私宅、料理店、使馆、船中,乃至浴室,随时展纸提笔;话题别无禁忌,上至天文地理、人文历史、博物医学、古典章句,宗教戏曲,下至名山大川、风情民物、时政要闻、民间习俗、时髦流行、贩夫走卒用语、扇页题字和漫画等,臧否人物,品评书画,说故实,谈乐论歌,几乎无所不包。有些问题,彼此谈论得还相当深入。整理这样一份跨文化的写本文献,需要包括历史和明治时代两国文化多方面的知识。
笔谈较之语谈更为简要。书写时有插空补字、连笔省形、涂抹污染、残损断裂、字迹不易辨认的情况。这些对于解读来说,都成为困难因素。黄遵宪等人虽然不会说日语,但笔下有时也会跑出几个汉字写出来的日语词。如“油罗须”(よろしい,好)、“划里”(わるい,坏)。笔误也常与日语读音相同或相近相关,如“先制人”写成“先征人”,盖因日?“制”“征”读音相同所致。这些都需要整理者格外留心。实藤惠秀整理本最后就对几个拿不准的地名和字形加以讨论,将释读的经过娓娓道来,每一字有每一字的解读故事。初不识“原”为何处,他结合地理考证,才知道“”乃“?”字草书;“阿玉池”的“阿”字因书写时墨汁滴落黑成一团而只剩下半边似是而非的“阝”;因为笔谈者将“赤贝”二字写成合体字“”,再加上写得潦草而让人摸不着头脑;因为将人名“兼吉”省作一字“兼”而很容易误认作“草”字。刘雨珍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除对原件中的笔误多加指出之外,还纠正了《笔谈遗稿》的不少释读错误。
疑难字固然需要精心考释,有些常见字,稍一疏忽,也会释读错误。《庚辰笔话》第七卷第四十七话黄遵宪说:“国家承平无事,才智之事无所用,故令其读书,所谓英雄入彀中也。”“入彀中”,或释为“人彀中”,则意反晦涩。已经出版的中文整理本中也还有尚需商榷的释读,还有缺字待补的情况。
画谈识趣
笔谈纸面之外,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信息源,那就是笔谈双方的表情。因为笔谈者是一边观察着对方的表情,一边决定下一步要写的字句的。书写中随时涂改,如果感到对方没有读懂自己所写的内容,就会想办法改进述说的方式。把要说的画出来,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这些笔谈资料除了文字之外,还穿插了一定数量的图画。笔谈者随谈随画,谈到什么画什么,以补充对话交流的不足,给对方更为直观形象的印象。对话者虽然并非
图六 书画一家让笔谈不再沉闷
都是画家,但汉字书写培养出来的运笔用墨的技巧和熟练,让他们可以展现从神话传说、《庄子?逍遥游》到中国建筑、陈设、用具、人物动作等多方面的信息。这一部分,就像书籍中的插图,是写本中不可缺少的,也是展示笔谈个性的极好资料。今天的中国人,可以据此了解当年的实物,也可以借此管窥早已消失的习俗。
对于没有机会跨出国门亲闻亲见的人们来说,单靠文字带来的想象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。江户时代隔海的日本人为了在脑海中描绘中国的实物,曾经请当时的画家根据赴日清朝商人的描述画图,《清俗纪闻》就是这样问世的。旅居北京的留?生青木正儿,也曾请民国的画家用笔画出北平正在消失的民俗,编为《北京图谱》一书。如果将笔谈中分散在各处的图画集中在一起,也可以看到当时文人观察与把握生活的一种态度。
画谈是笔谈的小配角。笔谈者非刻意作画,往往信手挥毫,寥寥几笔,意到为止,有时却颇为传神,令观者陡生联想。笔谈者中与几位很有漫画天才,几笔勾出的人物神形兼备。其中还有一位是赴日画家罗源。《罗源帖》中的画,很可能受到当时日本漫画的影响。作为美术史料,也有值得注意之处。如果在文字整理时略去这些部分,实在可惜,所以实藤惠秀整理本多处附上了这样的画。
诗谈逆志
写之不足,不觉画之涂之;画之不足,不觉吟之诵之。诗歌唱和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交谈,而且是最文艺的交谈;而批改诗文,则可以看成是批改者与原作者的对话。《文书》笔谈中的诗歌,犹如野花散乱于草丛,而第八册《书画笔话》更多为诗作,分书画筵、茶宴、赠友、赠美、课题、偶吟等,大河内辉声将其命名为“笔话”,可谓名副其实。
原作上的朱笔批改清晰呈现,诗文交流的细节由此一览无余。《偶吟》有一篇题作《史馆夜翻古书,与僚属校雠,即作,伏乞郢改,仍用史馆僚属铃木成章韵》的诗,是大河内辉声所作,请旅日文人王治本批改的。原诗用墨笔写成:
连榻两行灿烛花,校雠名籍赖名家。莫为散佚亡三箧,应使整顿满五车。玉轴频陈香木架,缥囊高曝竹竿叉。兰台日没倦吟读,好扇小炉烹苦茶。(又字韵未稳,然韵太狭,亦无典可用也。)
声和稿
古书史馆中,多散佚。盖保守之吏渐懈;编修之士不慎,把古书片片易毁拆者,而为涂鸦之看,仆蒙图书局也。长官即僚属,缓退官而勉为之,所以又此作也。
有朱笔在原诗上做了修改,现将修改后的诗歌抄录在下面:
检点云篇灿烛花,此书原是属官家。半残半阙遗三箧,且阅且披满五车。玉轴频陈香木架,缥囊高曝竹竿叉。兰台日落吟情倦,聊拨红炉烹涧茶。
同时,王治本还将跋中的“蒙”字,改作“被擢”。由此可以知道,大河内辉声1881年始任职修史馆,这是他任上所作。当时古书散佚严重,馆员松懈,编修之士亦不精心,书多损坏。这里所说的古书,当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汉籍。诗吐露出他对此的忧虑,也描绘了他夜晚翻阅古书的心境。对比一下原作与批改后的文字,文字上固然更好些,但原作中希望依靠专家整顿现状的心情表达得更为明白:“莫为散佚亡三箧,应使整顿满五车。”有了这一句,表明后面描写的夜读,是与整顿修史馆的心愿相联系的。遗憾的是,写出这首诗的第二年,大河内辉声就因患哮喘病去世,对整顿修史馆之事也就无能为力了。
诗词切磋,也并非中国文人的“单向给予”,黄遵宪等人也曾向日本友人请教。黄遵宪《日本杂事诗》完成后,曾请宫岛诚一郎、青山延寿、龟谷省轩、冈千仞等为其修改;他在撰写《日本国志》的过程中,也曾得到这些友人提供的资料。这些在笔谈中都有所体现。
面对这样的情况,一般整理后的本子,校记中会说明原作和修改的情况,这远不如看到写本原件更为直观生动。王治本边读边改,用字右侧红圈断句,字左下侧红圈表删除,而将所改之字朱笔书于字右侧。原件中的字形、用笔不同力度、字形、涂抹、圈批,甚至可以推测批改者思索的轨迹。阅读原件,即便是影印,也有与阅读整理本完全不同的乐趣。
中日韩诗文交流源远流长,以诗会友,早有传统,其中亦有关乎外交者。日本学者村井章彦曾撰《东亚往还 汉诗与外交》一书,梳理其事,而融书法、文学、绘画一体之现场感十足的资料,迄今为止,莫如此《文书》。此《文书》全部在华影印出版,让我们结识的中日文人,多达两位数,而其中让我们印象最深的,当是黄遵宪、何如璋、大河内辉声这些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印迹的人。这些笔谈就是他们向未来发出的不会消逝的声音。
或许有人会想到,大河内辉声费心费力保存下来的不过是几个文人个体的笔谈经历,到底有多大价值?这不能不说到写本学与传统的版本文献研究的不同。写本学研究的就是写本的“个体”,它肯定每一个作为历史遗存的“这一个”“这一件”写本在某一时点、某一传播环节的特有作用,这种作用是不以版本的存在而化为乌有的。群体往往是由一些看起来细微的鲜活个体结成的,“这一个”“这一件”的个性特点和独有魅力正是写本研究的立足点。诚然,每一写本、每一个体都不“等值”,但关注它们,分析它们,就能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文化面孔,而不是被条条化剪裁过的描述。
个体的精彩也是历史的风景。实藤惠秀在《大河内文书》付梓前,在扉页上写道:“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不断进行笔谈的珍贵记录。论文、作诗、问俗、话风流,这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,蕴含着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。”当时正处于日本文化潮大拐弯前夕,文人在这种朋友间面对面的笔谈时,往往道出很多不见于公开场合的个人见解,如对于汉学的价值、日本汉学功过和命运、对于当时人物、作品的评价等,这些对于黄遵宪等人的影响,就值得具体探讨。所以研究黄遵宪以及当时中日之间的外交史、文化交流史,具有唯一性的这些材料,可以说是无可再生的。
文化交流需要熠熠闪光的小个体,需要热心肠。大河内辉声等人不以语言不通为意,热衷于与清国外交官与文人以笔代口笔谈、并精心整理与保存,算得上超热心了,而在此后首先在日本整理出版的实藤惠秀,以及一直致力于将其传往中国的郑子瑜、汪向荣、王唯、刘雨珍、王宝平、王勇等结成的“接力队”,也都是热心肠。今天有了精美的影印本,又是一场新接力的开始。笔谈中的文字、图画和诗歌,都可以称为笔谈写本研究的课题。这些研究很可能给传统的文献整理带来很多新东西。
学术发展与文化交流一样的地方,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跑完全程。
(作者单位: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)